
近几年,一种以“秒”为节奏、以“爽”为内核的娱乐形式——短剧,正极强地冲击着我们的视野。它挣脱了传统影视的叙事框架,将矛盾冲突极致浓缩,那些高度程式化、套路化的桥段,精准戳中了当代人在碎片化时间里的情绪开关,成为当下最流行的“电子榨菜”,让我们在通勤路上、午休间隙,迅速完成一次从现实抽离的短暂“精神代偿”。
但随着短剧市场的繁荣,也带来诸如短剧是否是“下沉市场专属”、爱看短剧是否是低俗的文化品味等等的争论。本期我们特别邀请了三位作家朋友,作为观众也作为创作者,与我们分享看短剧的新奇观感与深度思考。
如果不是别人主动问起,我很少提及自己是短剧受众。
接触短剧是个偶然——最开始是一个广告弹窗,里面的故事很抓人,我以为是免费的,便一集一集往下刷,直到第35集,它突然开始收费。这部短剧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故事梗概也记得模糊。为此,我还上网搜了一下它的关键剧情,想找找第一部启蒙短剧的名字。我在搜索框里打下:“有一个女的,她是某个市的千金大小姐,只上到高中就辍学了,她爱骑小电驴到处走,还喜欢在街上卖烧烤。”打完这个句子,我自己都觉得这样的情节荒谬可笑。
后来我看得比较多的是徐艺真的短剧,比如《霍少闪婚后竟成了娇娇公主》《季总您的马甲叒掉了》《南总这次玩大了》,她经常和孙樾演对手戏。她的演技不错,情绪和表情都把控得很到位,但那几部剧的剧情、人物名字我完全没有印象了。
还记得有一次,我特意准备了一个短剧在抽血的时候看。我晕针,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在前面还有两个人的时候,就开始看《请君入我怀》。虽然平时我也有其他爱好,但我不相信那时候有任何人能比剧里被甜宠的女主宋瑶枝在府里放穿云箭召唤皇上,对我更具有安抚和麻醉作用,除非对面的护士是林俊杰本人。
我看的最后一部短剧是《闪婚老伴是豪门》,这部剧我隐约能记起几个片段。一是霸总喊石小秀的声音;二是石小秀的孙子办生日宴,她被赶出去,我忘了她有没有被打,如果真的被打了,我也不意外。

在短剧里,常常会有这样一个经典场景:主角被扔出他本不该进入的空间,通常是豪华酒店、KTV会所这类地方,被扔出去的瞬间,观众立马能共情一种“你等着”的心理。公式告诉我们,该人物一定会因为某种偶然,或是命中自带光环——总之不是靠自身努力和拼搏——再次以极其夸张的方式回到那个场景。他必定西装革履,金光闪闪,让当年鄙视他的那些人刮目相看。这种缺乏对人性与世界复杂性理解的设计,是短剧常被当作“低俗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闪婚老伴是豪门》以58岁的单身母亲石小秀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石小秀有一天无意中救了一个女孩,女孩作为回报,执意要将她介绍给自己的霸总父亲。婚后,为了考验石小秀,霸总父亲一直隐藏着自己的身份。
这样一本正经地写下《闪婚老伴是豪门》的情节,让我不止一次发笑——为我曾一度被这样“无脑”“毫无逻辑”和“简单粗暴”的情节吸引感到羞耻。当然,那些夜晚我也不止一次在观影过程中按下暂停键,羞愧地检讨着自己:“熬夜也就算了,你明明受过高等教育,怎么会相信这些情节啊?”这个问题很有用,它能让我在接下来的几集里自我感觉好多了:毕竟短剧还没有完全冲昏我的理智——我还知道自己在吃“垃圾食品”。
然而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为看短剧感到羞耻呢?我甚至还为“看短剧感到羞耻”而羞耻,因为我原本不应该为此感到羞耻。
后来我发现,我的这种羞耻感并非来源于短剧,而是所谓“知识分子身份”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张力。我之前并未意识到,这种羞耻指向文化资本、审美等级与艺术本质的讨论。如果说短剧是低俗的,那么“低俗”的定义是什么?“高雅”的定义又是什么?这些都是由谁来决定的?美学是否真的有一把永恒的标尺?
纵观文化史,我们会发现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二元区分由来已久。歌剧、交响乐、油画与古典文学,被视为“高雅”的象征。而通俗小说(如言情小说)、街头表演则被归入“低俗”的范畴。

摄图网AI生成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区分》中曾揭示过一个残酷的事实:品位并非纯粹的个人选择,而是社会阶层的标志。所谓的高雅品位实际上是社会阶层区分的产物,是上层阶级维护文化资本的方式。因此,高雅或是低俗的分界并非艺术的本质属性,而是社会建构,而我的羞耻感正是这种等级秩序内化为个体情感的结果。
那他说的文化资本又具体指什么呢?布尔迪厄这样定义,一个人通过教育、修养、文化实践而获得的符号性资源。比如我作为写作者、博士生的身份,使得我积累了偏向“高雅文化”的资本,我被期待展示所谓的“正统的品位”。而短剧的消费被视为一种“越界”,此种“低文化行为”造成了身份与实践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情绪逐渐以羞耻感的方式呈现出来,变成一种自我惩罚。上层阶级通过占有“文化资本”而确立审美标准,将通俗娱乐贬低为“低俗”,以此维护自身的文化优势。这种划分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游戏:当一个人宣称自己喜欢瓦格纳而不是凤凰传奇时,他不仅是在表明音乐偏好,是否也是在表明社会地位?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KTV里,我唱完一首《苹果香》又接着唱了一首《奢香夫人》,有个朋友给我录了像。回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视频里,无意中录进去了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耳语的声音,他问:“蒋在怎么老喜欢唱这种歌啊?”
后来为此我不得不慎重考虑:是否下一次唱完《奢香夫人》这类歌后,我应该紧跟一首歌剧《茶花女》的选段《祝酒歌》,像薇奥莱塔那样端着杯子,和朋友们一一干杯,以此来彰显我“辽阔”的艺术品位。
或许我们是时候,将所谓的“高雅”和“低俗”看成一场幻觉了。仔细想想,的确是这样:博物馆决定了将哪些画作展出;音乐厅决定哪些曲目被演奏;大学决定哪些文本被教授;奖项与评论体系不断制造着新的权威。这分明是哲学家、批评家、社会阶层、文化结构等共同缔造的幻象。这样想让我感觉好多了。因为我在整个过程中感到的羞耻感,不过也是一场幻觉。甚至我的“独特品位”,正象征着某种不确定意识的进阶。
或许在一百年后的某一天,短剧也会拥有不一样的文化姿态,甚至成为主流。每个时代,艺术总是被当成人类的最高创造,与此同时,人们一定会将某些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划入“庸俗”“不入流”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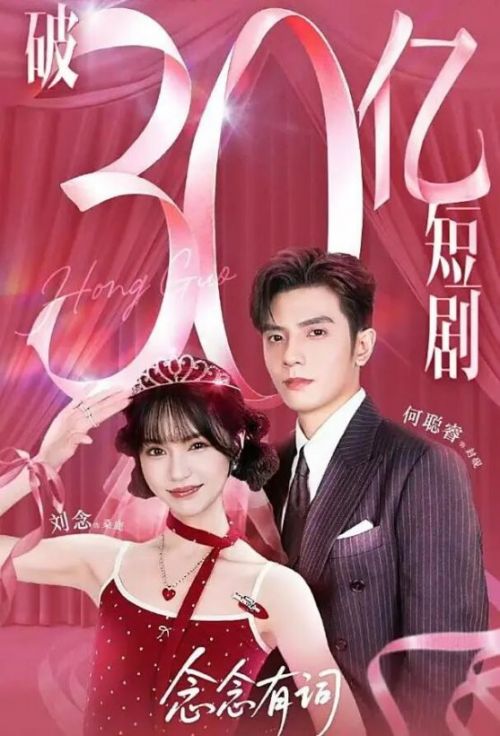
但如果我们真的深刻理解这段历史,会荒谬地发现:许多今天在神坛上供奉的经典艺术,几乎无一例外地曾经被认作“低端娱乐”。好像人类对于艺术的本能,总是奇怪地先排斥,然后再追认。
16、17世纪的伦敦,前来看莎士比亚戏剧的人大多是商贩、工匠以及小偷。当时的上流精英将莎士比亚戏剧看作粗俗、低级文化,不配与荷马或维吉尔的作品相提并论,里面充斥着下流笑话、血腥场面和滑稽桥段。然而,随着18世纪古典主义者的重视,以及19世纪浪漫主义者的再挖掘,莎士比亚被尊为世界文学巨匠。
包括后来小说的发展:17、18世纪时,人们以写小说为耻,小说被看作有害物质,会侵蚀人们的灵魂;而且当时的人还觉得,只有年轻人和妇女才会看这种廉价读物,它损害了人们的道德品质,因为小说缺乏传统史诗与悲剧的崇高性(这套说辞听起来有些像如今对短剧的攻击)。但到了20世纪,小说几乎变成了文学的中心。
而且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文化等级逆转不仅仅发生在文学场域,还发生在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之中,比如人们对歌剧、爵士乐的看法,再比如当年对印象派绘画的讥笑。所以,这好似某种规律,当新的社会阶层崛起,他们大概率会带来新的审美标准,重新定义整个艺术门类;他们的崛起也必定带来新的文化资本的再分配。
雅克·巴尔赞曾不断警示我们:文化从不在“直线式进步”,而是在“误解与修正”之间摇摆。不过,我仍然难以想象,一个世纪之后,《双面权臣暗恋我》《好一个乖乖女》这类短剧会与《荷马史诗》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讨论;想象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让我依然觉得荒谬而可笑。不过,那样的时代一定是个有趣的时代。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